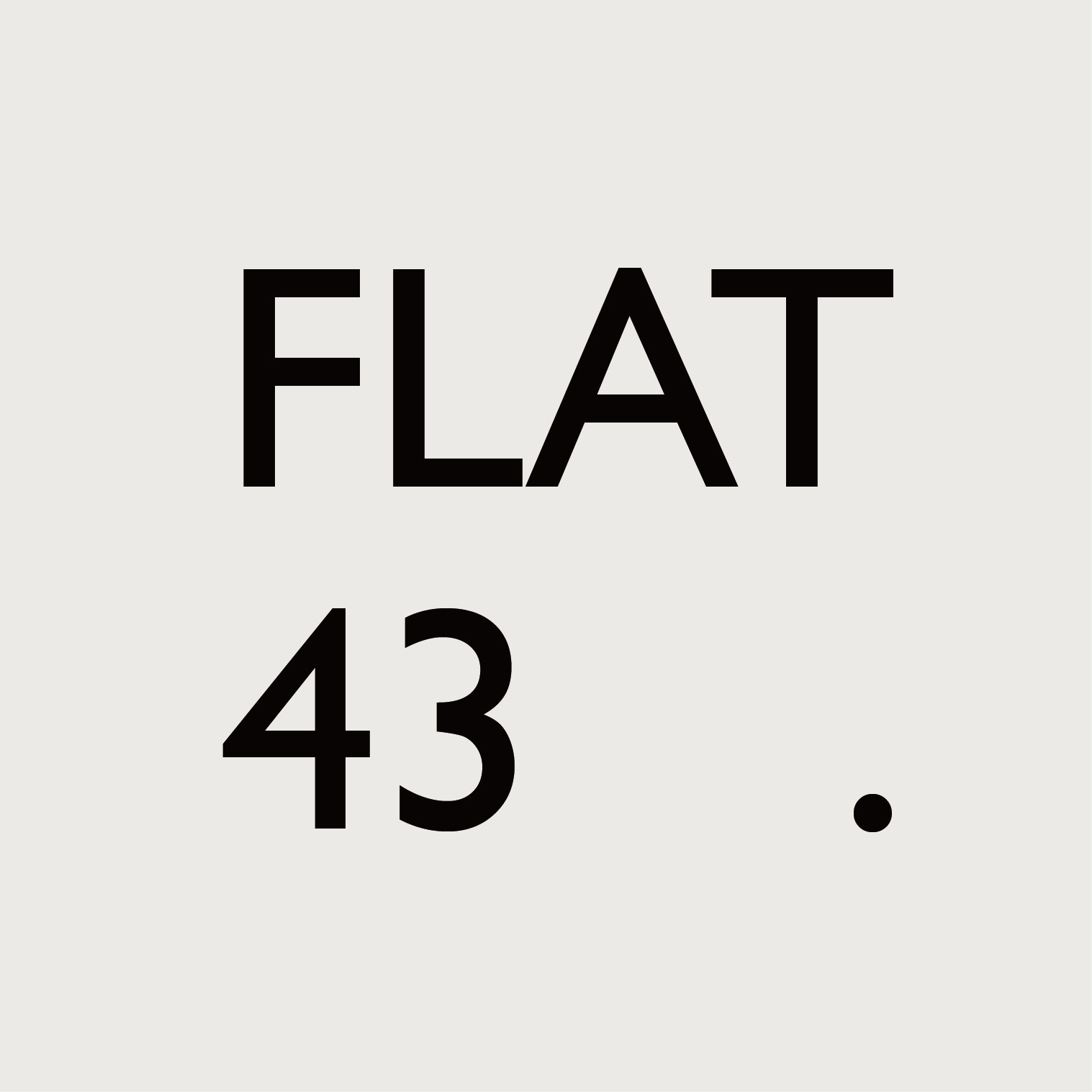「我說,我們就朝太陽的方向前進,看著日出日落,永遠就不會停止往前。」—— 〈藍色小貨車〉
自〈媽媽說〉到〈藍色小貨車〉,音樂藝術家宋楚琳(Erin Song)的歌曲總是透著善於感知的細膩,及情感滿溢的心意。如此獨特的創作特質,須從生長的起點談起——那位於高雄,不時令身在台北的她,頻頻回望的家鄉。
「要記得,家人間要相互扶持。」—— 藍色小貨車的後座風景
「父母一直對我們沒有什麼要求,只希望遇到困難時,要記得,家人間要相互扶持。」身為拉阿魯哇(Hla’alua)族一員,楚琳成長於一個龐大的家庭,光父親就擁有7位姐妹。一想起童年,記憶總是落在承載一家生計的藍色小貨車,「小時候常常躺在車後座,聽著爸爸播放各種類型的音樂,也無意間培養了聽歌的習慣。」
除維持家中雜貨店的營運,這台小貨車也肩負許多父親閒暇之餘的工作,如協助賑災、救護,其實每一次的搜救都是一種風險,家人總是在擔憂中渡過。「有一次搜救工作結束,貨車路過家中門前時,爸爸竟然還向我們揮手。」小時候對貨車的記憶總是讓楚琳好氣又好笑,在長大後,因為一場與已逝父親重逢的夢境,我們才得以遇見〈藍色小貨車〉這首思念滿溢的歌曲。
承襲家中處處替他人著想、照應彼此的溫暖性格,這個家也同時築起楚琳對音樂的想像。
自國小開始,只要校內舉辦歌唱比賽,往往少不了楚琳的身影,此時的她常常哼著族語歌,與支持自己的母親參加一場又一場表演和競賽。隨著時序前進,楚琳乘載著父母對教育的期望,國中便離鄉到市區就讀,成為少數寄宿學校的學生之一。許多因想家而失眠的夜晚,唯有在公用電話投下硬幣,才能與家鄉更靠近一些。
拿起話筒,「有時候並不真的想和媽媽訴說遇到的困難,只想聽聽她的聲音。」在百般難受的夜晚隔天,楚琳便會聽到學校廣播:「宋楚琳請至某處室領取包裹。」一打開,媽媽親筆書寫的信件和一箱沈甸甸的水果未曾遲到過,而這些瞬間,沈甸甸的還有楚琳眼中的淚。
「音樂不只是唱唱歌而已,它還能達成很多、很多好聽以外的事情。」
離家的日子,楚琳總會發掘許多類型的音樂陪伴自己。國中時期鍾愛著自然捲樂團、雀斑樂團;而高中則是確立自己欲以音樂做為職涯的啟蒙。
加入學校的音樂社團後,每每盼到長假,社上的慣例是一起搭上前往東部的車,到榮民之家進行「服務學習」。隨著〈野百合也有春天〉、〈恰似你的溫柔〉音樂行進,這些以音樂表演陪伴年長者與孩童的日子,讓楚琳深刻意識到,歌唱將會是一件帶領自己人生持續前進的元素,「音樂不只是唱唱歌而已,它還能達成很多、很多好聽以外的事情。」
為延續這樣的念想,楚琳在大學專注於駐唱工作,一週僅休息兩日。哼唱著Bob Dylan的歌曲,楚琳不合時宜的駐唱選曲總是讓老闆苦笑:「一首也好,可以在歌單中加入現下排行榜上的歌嗎?」隨著駐唱日子過去,然而,以往支持自己的母親卻不再抱持一樣的想法,期望楚琳能如同許多族人,找份如軍職般穩健的職涯。無法達成協議的兩人,在當時都不願和對方多說一句話。
靠著音樂有了些許存款,「雖然正在和媽媽冷戰,但有一天唱著唱著,發現自己遇到任何小事情都會發自內心的快樂,突然覺得現在這樣的生活,竟然還不錯。」楚琳笑說。一通電話回家,道了歉,訴說音樂所帶來的純粹快樂,兩人竟就一如往常有說有笑,好似什麼都沒有發生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