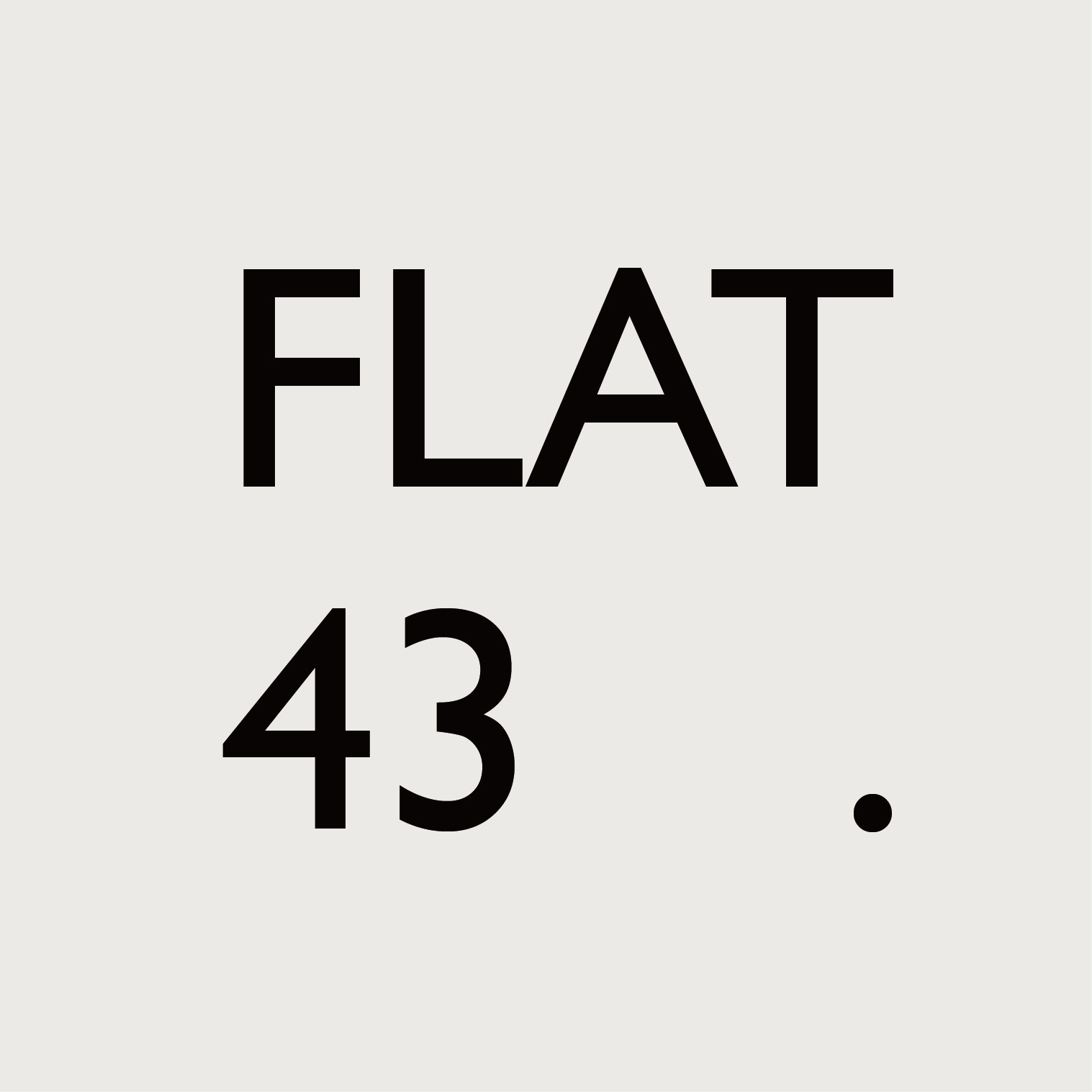В
йЈӣж©ҹз·©з·©йҷҚиҗҪеңЁдёүеҚғе…¬е°әзҡ„з§ҳйӯҜе®үең°ж–ҜзҫӨеұұд№Ӣй–“пјҢзңјеүҚжҳҜдёҖеә§иҰҶж»ҝзҙ…иүІеұӢз“Ұзҡ„еҹҺжұ вҖ”вҖ”еә«ж–Ҝ科пјҲCuscoпјүпјҢеңЁе…ӢдёҳдәһиӘһпјҲQuechuaпјүиЈЎж„Ҹе‘іи‘—гҖҢдё–з•Ңзҡ„иӮҡиҮҚгҖҚпјҲEl Ombligo del MundoпјүгҖӮеӮіиӘӘеӨӘйҷҪзҘһ Tayta Inti е°ҮеӯҗеҘі Manco CГЎpac иҲҮ Mama Ocllo иҮӘзҡ„зҡ„е–Җе–Җж№–пјҲLago TitikakaпјүжҙҫйҒЈиҖҢдҫҶпјҢжүӢжҢҒйҮ‘жқ–пјҢеңЁйҖҷиЈЎзӮәеҚ°еҠ еҠғдёӢжңҖеҲқзҡ„еқҗжЁҷгҖӮжӯӨең°йҖҗжјёзҷјеұ•зӮәеҚ—зҫҺжҙІзүҲең–жңҖеӨ§зҡ„еёқеңӢдёӯеҝғпјҢд№ҳијүи‘—13еҖӢжңқд»ЈгҖҒ400еӨҡе№ҙзҡ„иҲҲиЎ°гҖӮ
иҲҮиә«й«”е°Қи©ұзҡ„й«ҳеҺҹжҷӮеҲҶ
еңЁйҖҷиЈЎпјҢе№іең°дәәеҝ…й ҲйҮҚж–°еӯёжңғиҲҮиә«й«”е°Қи©ұпјҢеӣ зӮәжө·жӢ”й«ҳзҡ„й—ңдҝӮпјҢзӮәдәҶдёҚж¶ҲиҖ—йҒҺеӨҡж°§ж°ЈпјҢеҸӘеҘҪ緩緩移еӢ•пјҢиҰҒжҳҜиә«й«”дёҚиҲ’жңҚпјҢжңҖеҘҪжҳҜжіЎжқҜеҸӨжҹҜиҢ¶дҫҶиҲ’з·©пјҢиӢҘжғіиҰҒжӣҙжҺҘең°ж°Јй»һпјҢд№ҹеҸҜд»ҘзӣҙжҺҘе’ҖеҡјгҖӮ
еҸӨжҹҜи‘үеңЁеҚ°еҠ ж–ҮеҢ–дёӯпјҢдёҚеҸӘжҳҜдёҖзЁ®зҷӮеӮ·зҡ„и—ҘиҚүпјҢе®ғд№ҹеғҸйҰҷиҸёиҲ¬жҲҗзӮәзӨҫдәӨзҡ„еӘ’д»ӢгҖӮдәӨжҸӣеҸӨжҹҜи‘үж„Ҹе‘іи‘—гҖҢжҲ‘еҖ‘д№Ӣй–“жңүдҝЎд»»гҖҚпјҢиҖҢеңЁдҝЎд»°дёӯпјҢдәәеҖ‘жңғе°ҮдёүзүҮеҸӨжҹҜи‘үз–ҠеңЁдёҖиө·зҘӯзҘҖпјҢзЁұзӮәгҖҢkвҖҷintuгҖҚпјҢиұЎеҫөе®ү第ж–Ҝдёүз•ҢпјҲдёҠз•Ң Hanan PachaгҖҒдәәз•Ң Kay PachaгҖҒең°дёӢз•Ң Uku PachaпјүпјҢз”ЁдҫҶ敬зҚ»зөҰзҘһйқҲгҖӮ
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