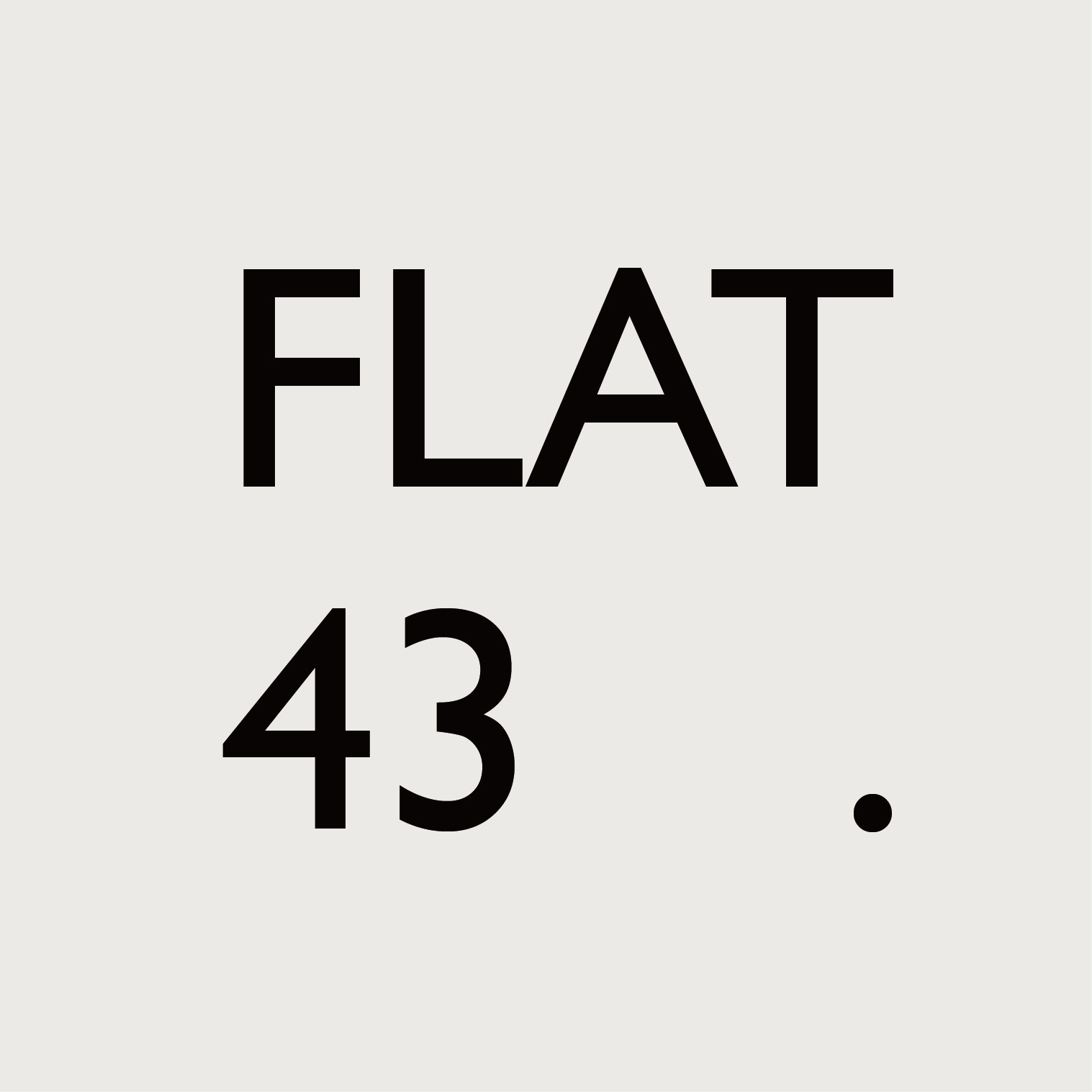小心翼翼卻也篤定地,小女孩唐突的手指探進主臥室櫥櫃一疊相片中抽出幾枚,那些家族成員的身影應該和外人無關才對,但有些事物的意義無以名狀,只知道若與人分享好像就會更閃亮一些。相片太迷人,當然也值得悉心挑選,再用角貼固定在卡紙上鋪排成冊帶在身邊——編輯攝影書講究的膽識、直覺都無師而自通,小女孩甚至把其中幾枚當禮物分送給學校的修女。
雖然下場是被父親教訓一頓,但 11 歲那年,她仍得到一台屬於自己的相機。
一手感受著飛機窗和景色的距離,一手緊抓布朗尼相機,這只深色小盒子對離家去上寄宿學校的少女而言,意義或許更接近行李箱,人生旅途上邂逅的奇觀、象徵、風景的情緒甚至鋪天蓋地的生與滅都寄託其中,從墨西哥到跨越陰陽各地,連同遭遇這一切的自己一起收進黑白畫面裡。
終於在路上彎起手指又鬆開,沿途顛簸,她迎著洶湧到夢境也為之扭曲的荒野眨眼再眨眼,刻下記號。從今以後,她要把一切都呈現出來。
2025 年,年屆 83 歲的 Graciela Iturbide 首度在日本舉辦生涯回顧展,隨京都國際攝影節 (Kyotographie) 在市立美術館別館亮相。
攝影節年年將城市中各色場館串連成展,主題與空間互文的方式向來內斂,就像前身是京都市公會堂東翼的古老別館,屋簷融合了常見於古城、寺社的破風元素,散發出坦然披戴滄桑的氣質,一踏進去,就能感受到藝術家如何和異國相見恨晚,又如何以文化對話。
端正的展廳內,兩兩一組的木展板糊上日本傳統和紙再塗布紅土般的顏料,彼此間留有縫隙,供角度精準的光落地形成透明的沙丘;視線匍匐穿行,彷彿目睹中南美洲的荒漠中輪番升起一幅又一幅異象,把白盒子調度成一方立體的攝影集。這是身為建築師的 Mauricio Rocha Iturbide 繼墨西哥的紅磚攝影工作室後,再度親手為母親的作品打造的現身場域。
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
童年時偷家庭照自製藝術家書籍 (artists' book) 的 Iturbide 大學時代主修了電影,畢業後仍一頭栽回靜態攝影世界,一轉眼已和底片相機相伴 60 載,原因是「電影比較像小說,而照片如詩」。
詩講究格律,無論追求套著枷鎖跳舞或衝撞框架,都是在意識到既定環境的情況下提煉出種種意象,如雙面鏡般一面引用來歷,一面映射出無邊的想像。所以說,什麼樣的景觀會讓人一接近就墜入意象的雲霧之中?
以 Iturbide 出生成長的墨西哥城來說,那是個在社會動盪中擁抱生命的所在,處處保留著前哥倫布時期的寶貴歷史,保守價值觀依舊根深蒂固。即使形象如此鮮明,她仍當局而不迷,懷著探索者的視角住進胡奇坦小鎮人家,和流傳千年的薩波特克文明朝夕共處。由於當地是母系社會,除了禁止男性涉足市場,集跨性別價值於一身的特殊身分 "Muxe" 也應運而生;其中一位主動邀 Iturbide 回家,換上女裝後在鏡頭前舉起明鏡,當〈Magnolia with Mirror〉剛柔並濟的側臉浮現,那一幕,邊緣性別認同不得不交手的禁忌、解放與悲歡糾葛都不過是牆上的斑駁,絲毫傷不了這抹玲瓏的自由魂。
上市場時,Iturbide 也不搜集民情雜沓或報導具體事件,倒是特寫了頭頂盤錯著鬣蜥的婦女,神色從容深邃,在恰到好處的深濃背景襯托下,〈Our Lady of the Iguanas〉儼然統治過不朽王國的君主正凜然接受仰望。
70 年代末期受國家原住民研究所 (INI) 委託而深入墨美交界,她隨塞里族部落遊牧數月,無意間拍下族人提著收音機走向蒼茫的瞬間:〈Angel Woman〉長髮飛揚,披肩如羽,在那片僅剩 500 多名族人居住的沙漠中,傳統的象徵就這樣從畫面一隅悄然現身,跨過雜草,拎著能飛越藩籬的媒介大步向前,走向科技與資本主義聲聲呼喚的新時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