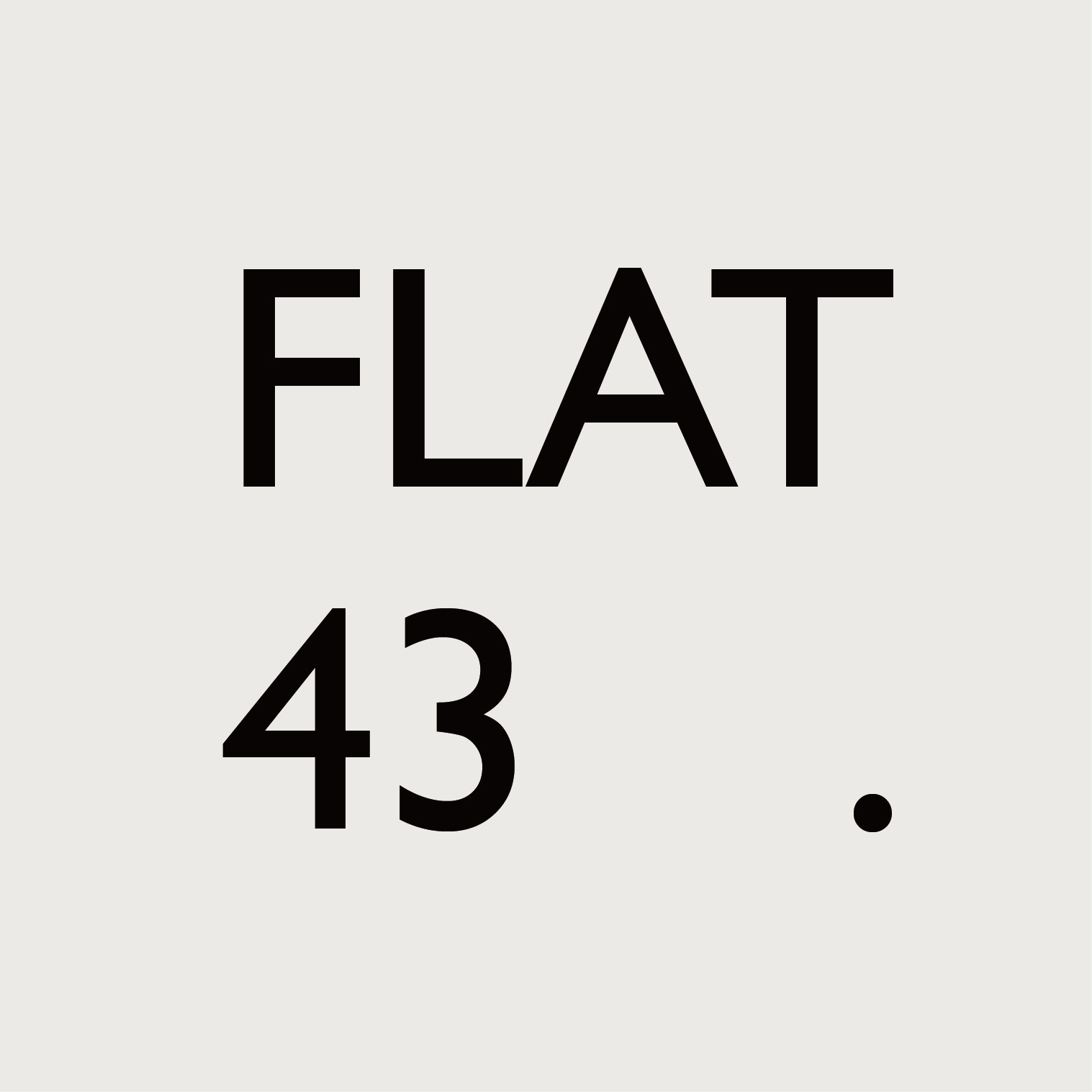дЊѓе≠Эи≥ҐзЪДгАКеНГз¶ІжЫЉж≥ҐгАЛеЬ®е§ІйКАеєХдЄКжШ†пЉМиИТжЈЗзЪДжЧБзЩљиБ≤зЈЪеГПйЬІж∞£иИђжї≤еЕ•жИСеАСиА≥жЬµпЉМйЦЛе†ізЪДжЕҐеЛХдљЬз©њиґКдЄ≠е±±йЂШзЪДиїКжµБпЉМйЬУиЩєзЗИиИЗиїКзЗИеЬ®йїСиЧНиЙ≤зЪДе§Ьи£°жЛЦеЗЇйХЈйХЈзЪДеЕЙе∞ЊгАВйЫїељ±зХЂйЭҐе∞ЗзХґжЩВеП∞еМЧе§ЬзФЯжіїзЪДжГЕжДЯиИЗж∞ЫеЬНжњГзЄЃеИ∞ж•µиЗіпЉМз≤ЊжЇЦеЊЧеГПеЬ®жМЙдЄЛењГиЗЯзЪДжЯРеАЛйЦЛйЧЬпЉМдЄАзЮђйЦУиЃУдЇЇиБљи¶ЛеЯОеЄВзЪДиДИеЛХиИЗйЪ±зІШеСЉеРЄгАВиІАзЬЊеГПеЬ®з™ЧйВКзЬЛиСЧеЯОеЄВзЈ©жЕҐзґУйБОдЄАж®£пЉМйЂФй©ЧеНГз¶ІеєіеП∞зБ£еЬ®зєБиПѓиИЗз©ЇзЩљдєЛйЦУзЪДжЄЄзІїгАВйВ£жШѓдЄАз®ЃйЫ£дї•и®АеЦїзЪДеП∞зБ£зЖЯжВЙжДЯпЉМзФ±зХґжЩВзЪДз§ЊжЬГж∞ЫеЬНгАБжФњж≤їгАБеХЖж•≠иИЗз§ЊжЬГжіїеЛХе°СйА†иАМжИРпЉМж≤ЙжЊ±еЗЇе∞Ие±ђжЦЉйВ£еАЛжЩВдї£зЪДжДЯжАІгАВ
йАЩз®ЃжГЕзЈТжШѓж®°з≥КзЪДпЉМе§ЦдЊЖжµБи°МжЦЗеМЦйЫЦзДґињЕйАЯйА≤еЕ•еП∞зБ£пЉМдљЖеНїж≤ТжЬЙеЃМеЕ®еПЦдї£еП∞зБ£зХґжЩВзЪДз§ЊжЬГж∞ЫеЬНпЉЫеФ±зЙЗи°МзЪД詶иБљиА≥ж©Яи£°еВ≥дЊЖйЩ≥зґЇи≤ЮгАИйВДжШѓжЬГеѓВеѓЮгАЙгАБеЉµйЬЗеґљгАИжДЫжИСеИ•иµ∞гАЙгАБиМГжЫЙиР±гАИж∞Іж∞£гАЙпЉМж≠Ми©Юи£°зЪДиЗ™жИСжЗЈзЦСгАБ姱жИАиИЗжЄЄзІїдЄНеЃЪпЉМиИЗйЫїељ±дЄ≠еПНи¶ЖеЗЇзПЊзЪДжЉВжµЃйП°й†≠зЫЄдЇТеСЉжЗЙгАВ
йВ£жШѓдЄАз®ЃиЗ™зФ±зЪДз§ЊжЬГ饮ж∞£пЉМжИСеАСеПѓдї•еЬ®еЗМжЩ®еЫЫйїЮиµ∞еЗЇйЕТеРІгАБеЬ®дЊњеИ©еХЖеЇЧи≤ЈдЄАжЭѓжПРз•Юй£≤жЦЩгАБеЖНеЫЮеИ∞жЬЛеПЛзЪДеЗЇзІЯе•ЧжИњйЦТжЪҐиБКеИ∞姩䯁пЉЫеСЉжЗЙзЪДдєЯжШѓдЄАз®ЃжЈ°жЈ°жЖВеВЈпЉМзґУжњЯеЬ®дЇЮжі≤йЗСиЮН饮жЪіеЊМзХґжЩВжБҐеЊ©еЊЧйВДдЄН姆еЃМеЕ®пЉМдЇМеНБе§Ъж≠≤зЪДеєіиЉХдЇЇе§ЪеНКеЬ®иЗ®жЩВеРИзіДгАБжЩВиЦ™еЈ•дљЬиИЗзђђдЄАдїљдљОиЦ™ж≠£иБЈдєЛйЦУеЊШеЊКпЉМжИњеГєиИЗиЦ™и≥ЗеЈЃиЈЭйЦЛеІЛжЛЙйЦЛпЉМеЯОеЄВзЪДе§ЬзФЯжіїзЬЛдЉЉзєБиПѓпЉМеНїжЙњиЉЙиСЧе∞Не§ЦдЊЖзЪДдЄН祯еЃЪжДЯгАВ
зХґжЩВзЪДз§ЊдЇ§еЬИеЫ†зґ≤иЈѓеЙЫиµЈж≠•иАМиЃКеЊЧжЫіеИЖжХ£иИЗдЄН祯еЃЪзЪДеєідї£пЉМзД°еРНе∞ПзЂЩгАБе•ЗжС©еЃґжЧПгАБBBS е∞ЗжЬЛеПЛжЛЙйА≤дЇЖзЈЪдЄКпЉМеНїдєЯиЃУдЇЇжЫіеЃєжШУеЬ®зПЊеѓ¶дЄ≠姱иБѓпЉМжЦЉжШѓжГЕжДЯеЊАеЊАдЄАжЩВйЦУйЫ£дї•жКТзЩЉпЉМжЗЄз©ЇзЪДзЛАжЕЛдЄ≠иЃУж∞£ж∞Ый°ѓеЊЧжЫіеК†е£УжКСгАВ
 
еНГз¶ІеєізЪДз§ЊжЬГж∞ЫеЬН
1996 еєідЄЙжЬИзЪДжКХз•®жЧ•пЉМеП∞зБ£й¶Цжђ°зЄљзµ±зЫійБЄпЉМжКХз•®зОЗйБФеИ∞ 76.04%пЉМзХґжЩВзЪДж∞СдЄїжіїеЛХдЄЛпЉМеВ≥еЦЃеЬ®жЙЛиИЗжЙЛдєЛйЦУзњїй£ЫпЉМеГПжШѓдЄАе†іеЕ®е≥ґеРМж≠•зЪДи°Чй†≠еДАеЉПгАВеЫЫеєіеЊМзЪДдЄЙжЬИе§ЬжЩЪпЉМж∞СйА≤йї®й¶Цжђ°еЯЈжФњзЪДеЃ£еЄГйАПйБОжЦ∞иБЮеП∞иЈСй¶ђзЗИдЄНжЦЈйЦГеЛХпЉМиЮҐеєХи£°йЩ≥ж∞іжЙБиИЗеСВзІАиУЃзЂЩеЬ®еЛЭйБЄиИЮеП∞дЄКжПЃжЙЛпЉМиГМжЩѓж؃紆зЩљзЫЄйЦУзЪДзЂґйБЄеЄГжҐЭиИЗй£ДеЛХзЪДйї®жЧЧпЉМеП∞дЄЛйЂШиИЙиСЧгАМйШњжЙБиРђж≠≤гАНзЪДе°СиЖ†е∞ПжЧЧгАВ
еП∞и¶ЦжЦ∞иБЮзЪДйЦЛз•®жХЄе≠ЧеЙЫиЈ≥йБОдЄАиЉ™пЉМе∞±иҐЂиљЙеИ∞ MTV еП∞зЪДдЇЮжі≤ж¶ЬеЖ†иїН MVпЉЫиГМжЩѓи£°зЪДеї£еСКжЩВжЃµжПТжТ≠йЫїдњ°ж•≠иАЕзЪДжЦ∞и≥Зи≤їжЦєж°ИпЉМе∞ЗгАМй¶ЦжЬИеЕНи≤їгАНиИЗгАМзД°йЩРйАЪи©±гАНзЪДеї£еСК襀еИЗйА≤йАЩе†іжФњж≤їиИЗжµБи°МзЪДжЩЪйЦУжЩВжЃµгАВйАЩжШѓдЄАз®ЃжФњйї®жЫіињ≠иИЗе®Ыж®ВиЉЄеЕ•дєЛйЦУзЪДйБОжЄ°жДЯпЉМжФњж≤їиИЗжµБи°Ме§ІзИЖзЩЉж≠£жШѓеНГз¶ІеєіеЙНеЊМеП∞зБ£з§ЊжЬГзЪДж∞ЫеЬНгАВ
2001 еєіеП∞зБ£ж≠£еЉПеК†еЕ• WTOпЉМиµ∞еЬ®еП∞еМЧиїКзЂЩзЪДжЦ∞еЕЙдЄЙиґКпЉМе∞ИжЂГи£°е§ЪдЇЖйА≤еП£йЫїеЩ®еУБзЙМпЉМSonyгАБPanasonicгАБй£Ыеȩ浶пЉМиИЗйБОеОїжЦєж≠£еОЪйЗНзЪДж©ЯйЂФ嚥жИРйЃЃжШОе∞НжѓФпЉМзХґжЩВзЪДзђђеЫЫеП∞еЬ®еЃґеЇ≠жї≤йАПзОЗиґЕйБО 80%пЉМеЕ®зРГеМЦзЪДеХЖеУБжµБйАЪдєЯж≠£ињЕйАЯеЬ®еП∞зБ£иФУеїґвЛѓвЛѓ